何向阳:开放的向日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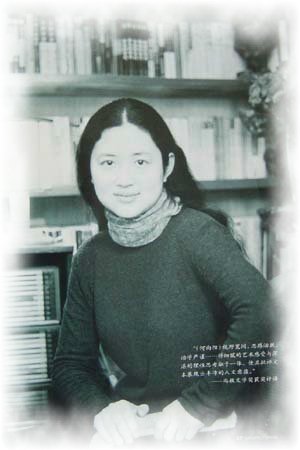
1、当年你进入大学学习时,中文专业是你的首选吗?
何:中文专业是我的首选。主要源自于我对文学的偏爱。高中二年级分班时,就读于文科班。当时就喜欢中文,原因很多,主要是受家庭环境影响。小学开始读苏联的小说,读《红楼梦》,常被宝黛那种纯美的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其实在初中时,由于崇敬居里夫人而喜欢物理,有种要当物理学家的冲动。后来仔细想一想,是当时爱读居里夫人二女儿写的《居里夫人传》(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她的精神感动,更被书中的文采打动,好的文学作品借助文字的力量表达出许多优秀人物的思想和品行,特别是人物传记类的书籍,更能震撼人的心灵。这种文字功夫,那时只是通过中文系的选择作为第一步的实现。
2、你的父亲是知名学者,母亲是位美术工作者,在你的成长及创作过程中,受他们影响吗?
何:作家、美术家可以划分在一个大类里,都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刻画人物正直的品格,高尚的情操。记得当时家里有许多苏联、俄罗斯的小说,父亲就推荐给我读,父亲常说宁读一本好书,不读十本坏书。记得当时一本叫《海鸥》的书,对我影响较大,书中描写了战争时期女主人公那种个人命运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相融合的英雄主义,对人性美的刻画,追求那种很高的境界,对我影响很大。我母亲是学油画的,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画画,常到近郊去写生,在家里举办过个人画展。对生活当中美的感悟的东西接触较多。
2、在你某篇文章中曾提到过"知童"一词,对那个特别时期,你印象深么?
何:确实我发明的,无论是当时的文学作品,还是社会上的词典里,都找不到这个词,它是相对于知青而言的,我3岁随父母下放置,知识儿童是指那样一个背景下一方面父母的知识分子身份, 一方面是个人身份――我在那里从5岁入学读了1年半的小学,69-73年是在河南南阳西峡小水下营生产队里渡过的。风景绝美但生活艰苦。大山十八里盘,非常险峻。我们是乘一大卡车去的,关于那段经历,我后来写成了《下放》一文,发表后,被多处转载,《华夏》杂志一出,"知童"一词就传开了,有的转载题干脆改成《我当"知童"》,在那个特殊时期,特定的地理位置,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更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不小的群体,许多像我一样家庭的孩子在农村渡过了他们的童年,苦辣酸甜,岁月给的,他们长大成人,内心结构和乡村孩子、城里的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对于生活的最早记忆是应该在历史上有一笔记录的。这可能是我发明"知童"一词的一个动因。我想往读到更多的他们的记忆。
4、有人说,创作有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要与文中的人物或事件同悲同喜,你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吗?
何:确实是有一种同悲同喜的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从事文学批评,始终认为批评是一个创作过程,它不但是一个对一种文学的解读,一种平面的阐述,一种引申,一种诠释,而是读进去融入到阅读中去,有感情因素,有主观的东西。传统文学批评认为,批评者是一个客观者、非常理性的、居高临下的、局外人的态度。但我一直想把它当作是一种创作和创造,在其过程中,把自己情感融入进去,追求批评家和批评对象的一种共振关系,心灵上的互动和回应,批评者是一个创作者,创作的空间确实很大,把创作者和批评家的心灵感应放在一起,与作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又有一种感应,是一种交响的过程,很多时候是一个交响乐,譬如我的《12个:1998年的孩子》,评述的中国当代优秀作家莫言的小说,他的《拇指拷》,其早期《秋千架》《枯河》都在描写孩子童年的经历时注入了一种更深度的东西,1998年发表的小说《拇指拷》描写了一个孩子给母亲抓药回来受到的挫折,被人捆到了树上,路人没有人解救他,很冷漠的遭遇,孩子为了早回家给母亲治病结果把两个大拇指给咬断了,挣扎回到他温暖的小屋,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小说尽管不全是现实发生的,有着浓郁的象征文化寓言意味,但是作家蘸满心血,有很深的东西,一种人道关心孩子的主题。做为评论者,无法作为一个法官、旁观者作客观上的评述,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我才去评述它,有作家的痛苦,解读上的建设,真正的批评,有感情主观上的出发,也融入了我的痛苦。这是一种完成,一种交响的东西。
5、你欣赏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何:对这个人问题,我有时也是矛盾的,我喜欢宁静,寂寞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静思,做出更加有深度的评述,但有时你要感受生活的变化,要走出书房,突围出去,比如说,去年走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沿黄九省,便是对宁静的一种突破,回到一个本来,一种原态,一种很开放的状态,亲身经历,泰戈尔提出过"亲证"一词,就是要你去亲自感受和证实,惟有此,才能获得真实。我以为,就是现在,也是相当可贵的一种思想。
6、网络时代里,有的评论家和作家对网络不屑一顾,你怎样看待后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冲击?
何:网络进入生活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网络文学也是文学门类当中一种新型的形式,而且现在网络文学也非常活跃,它充分体现了自由的思想,这样一种开放的时代,这样非常活跃的一种状态,肯定要求文学的形式不是一种,比如说上海有一个网站叫《榕树下》, 搞的比较好,网络文学对经典文学当然存在一种冲击,但很可能经典文学也存在着它自己的一种缺陷,比如过于雕琢,过于跟自然的,天然的状态离的越来越远,进入一种经典,书斋化后可能离人们的整个情感、认识远了,它可能也潜存这种问题。所以网络文学我觉得弥补了这样一种不足,它是一种新鲜的,生动的,非常活跃的一种东西,当然网络文学也存在它的一些缺欠,毕竟刚刚开始,它可能有一些过于随意,一些深层的东西不够,在整个文学性方面还达不到一种高度,但是我觉得两者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的,这种冲击对传统文学还是一件好事。
7、你用电脑创作吗?
何:电脑操作我还是比较初级的,就是打字,写文章直接在电脑上写,我觉得电脑创作空间可能很大,就是从文学来说,空间也比较大,从其他的方面,以后电脑还可以创作电影,音乐。像严锋《好玩》文章里写的,它游戏的空间也大得很。比较起来我还没有这么开发它,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初级状态,电脑对我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因为它特别容易炼字,就是打出来一个字,突然出现一个词,这个词你可能就从来都没用过,如果是用手写的时候,你可能用一个现成的什么,字思维,是电脑带给我的。手写的话,一些事情是一个意思,但是在电脑上写,感觉非常精炼,有一种炼字的感觉。我接触电脑在92年底。还不错,现在换了三台。炼字的感觉一出来,它其实在参与我的创作。
8、作为文艺评论家,你对来自不同媒体的文艺作品,都能摆脱专业的审视目光吗?
何:文艺评论家一般来说有一种职业病,审视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他用专业的眼光去审视。但是有例外,比如我个人,可能对文学要求比较苛刻一点,敏感一点,但是对音乐就无法用那种审视的目光,我经常被它感染,有一种天外来音的感觉,有时候在心里发生的那种震动无法用文字把它落实到评论表达出来。我觉得对一些具象的东西,可能文字,绘画、摄影,好象还无法摆脱那种审视,所以有时候可能对它要求苛刻一点,因为我除了文学评论外,也搞艺术评论,但是音乐,我觉得确实是让我在这个专业之外找到一个非常大的心灵沉淀的这样一种空间,比如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我听它,非常沉浸下来, 无法再去站在它外面,再去挑剔它,已经被它裹挟而走,已经被它整个包容进去了,人在那时候是,个人的东西是非常渺小的,只能是一种体味,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例外。
9、你对文艺作品的批评,有选择的标准吗?
何:我原来对作品的选择还是比较窄的,就是喜欢哪一类就去评论,比如说原来对张承志,我喜欢那种英雄主义的、非常坚韧的,硬汉精神的,包括海明威,整个下来的这样一个线索,有一种开拓性的这样一种人格,一种高贵的人格的东西。我选择的比较多,后来我觉得还是有些突破,进入视野的多,当然仍有选择的标准,标准是能否使自己阅读时发生感情共振。如果他写的东西使你发生了一种感动,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你想传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感动,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象二传手的一个过程,二传手就是把那个球传出去,让别人打的更好。就是说,他呢不单纯是一种传递,它是一种给它发展,就象泡茶似的,作品是茶叶,文学批评是水,把浓酽度给它化开了,然后就是让读者去喝。最后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味道,因为你要是吃干茶,喝矿泉水,都没有味道。这两者互融,融解到一起,然后读者才能更深的领会很多可能作者没有传达出来或者作者暗藏在冰山下面的那样一些东西。我觉得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跟自己心灵上有没有共振的关系,感动自己的。
10、你的作品理性、细腻,你经常会被一些文艺作品所感动而流泪吗?
何:对,确实,有人说我,评论是理性和细腻,一般理性都是粗线条的,但是细腻它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后者是很多人评价女性评论家具备的东西,但是身为女性好像很难具备理性的这样一种东西,很多人看到了我文字中的理性这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流过眼泪。李亚,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一短篇小说叫《被胡琴燃烧》,写一个孩子特别喜欢音乐,但是他非常穷,连个胡琴都买不起,然后他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个胡琴的主人锯木头啊,把自己家鸡卖了,然后又把猪什么的都卖掉,凑那个钱,结果还是凑不够,最后这个孩子宁愿把自己小拇指砍了,也要去换那个胡琴,这是成年人做不到的,只有孩子才这么纯粹。为了一件心爱,不惜生命也要得到它。我看了之后,感觉尤其是从理性的分析来说,七十年代生人,很多作者写东西都带有一种青春期的调侃,反叛,这些也无可厚非,因为它在成长的时候的一种叛逆心理,但是在李亚那里这些东西都没有,非常沉静,非常唯美,让我感动,为它流泪。不光文学,电影,音乐,只要里面交织了人物命运的,为之动容就绝不是件害羞的事。
11、不少读者对作者作品的阅读兴趣是看了相关评论后才引起的,你的文艺评论是原创者思维的再延伸吗?或者是客观评述呢?
何:这个跟前面的问题有一定联系。文艺批评也可以看做是原创作思维的再延伸,再延伸里头就有很多文章,它是怎么一种再延伸。它其实是把自己的东西跟作者、原创者的两种思维交织起来,产生了新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一直是对这种客观评述,当然客观评述我觉得是评论的一种基础,但是它确实不是评论的最高的一种境界,我认为最高境界的评论应该是感动人的,有感染力的,应该是一种精神的再延伸。
12、你喜欢什么颜色?
何:蓝色。我喜欢大海。
13、平时喜爱读哪一类书?
何:传记。最喜欢读传记,因为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传记,《拿破仑传》,《邓肯传》《甘地传》。还有《居里夫人传》。一直在读传记,好象它起到一种励志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关心人,人在那个他的一种历史阶段里头,他能走的有多高,能够走的有多远,无论他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他能够,在他那个领域里头,在他那个时代的限定局限里头,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人的境界,我觉得这个是我评论里头也一直比较关心,另外我觉得人生可以从中找到借鉴。
14、你生活圈子大吗?和朋友沟通和交流多吗?
何:原来圈子还是比较小的,基本是大学、研究院一些朋友,这样一个学者的圈子。但从去年走黄河后,一下子扩大了。沿途走了九省,接触了很多朋友,前几天还有一个从河南渑池来的一个朋友,是我走黄河交下的一个朋友,他专门跑过来想得到一本我写的黄河的书的。交的朋友各个层面都有,原来是非常封闭,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圈子。现在有农民,村里的孩子。
15、你有追星族吗?或是崇拜者,你经常收到他们的来信吗?
何:收到朋友的信是经常的,就象刚才我谈到的。包括这次到西北去,在大 河 家认识了写诗的,还有写散文的一些朋友,回族的一些朋友,他们把他们的诗歌散文寄过来,另外还交了一些象初中、高中生,他们是比较爱写信的。我也常寄一些书给他们,因为他们在山区里头。一个孩子比较喜欢乔丹,我就买了《乔丹传》,给他寄去,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来信非常多。
16、你如何看待缘分,友情?
何:友情缘分,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一求的时候都搀杂了其他的利益在里头,但是我觉得比如说非常自然发展的友情随着时间的迁移,非常自自然然的,象酒酵那样一种,我觉得那样是一种真醇的,就是没有任何利用或者是交换。它是一种比真正的友情。
17、喜爱电影吗?独自一人或更喜欢有朋友陪着?
何: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看电影。从小看到现在。那时侯看露天电影,两边都可以看,搬个凳子。现在电影院发展的非常好,郑州就有非常好的电影院。一个人,朋友陪着,都有。电影其实在用一种全面的形式说文学没法说的东西,它是一个集体的多元素的综合,文学只有文字,比较干枯,没有音乐,场景,电影最体现艺术的这种全景的展现,感染力非常大,把人的全身心都调动了起来,喜怒哀乐都最充分的表现出来。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有,知道哪个电影上映了,骑着自行车去看。看的时候,有时候整个电影院也就十来个人,能够感受到许多东西。可能最喜欢看的还是文艺片。
18、你也认为世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吗?
何:我认为还是有永恒的朋友的。利益可能不会有永恒吧,利益只是暂时的,因为利益是需要一种场合的,它要交换,要互惠,这样一种,他是需要一个场合的,需要两方的,比较商业,商业化的东西永恒是难的,它是说今天你受益,明天我受益,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吃白吃的午餐,就是说没有永恒的利益。但我觉得朋友还是有永恒的,一个朋友,在危难时候,在失意时候,在高兴时候,都能想到他,他呢,能够不管是在电话里,还是到你身边来,能够给你安慰,鼓励,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是非常好的。朋友是有永恒的。当然永恒的朋友这种境界是比较高的。
19、你认为行走文学有生命力吗?你打算走下去吗?
何:行走文学这个概念现在引起一些争议,就是主要来自有些读书界,当然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推敲,但是作为它所代表的那种行动的精神,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的,我认为是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就是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一个文人他不但是要读书,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觉得这种文化里面在倡导一种实践的、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呢,我觉得是,它可能跟西欧传统文学不一样。比如说《史记》,司马迁,他当时在写史记之前做的这种准备,这次我们去绍兴,到那个他去过的大禹陵。司马迁的老家是在韩城,陕西,就是黄河晋陕峡谷那个出口的地方,但是他能够,在当时没有现代交通的情况下,靠行走,靠走路,然后走到了江南,走到那儿去看大禹,其实大禹本身他也是一个行走的人,他治淮河,治黄河,他脚底板底下都长满了茧子,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样一些传说,就是从神话传说开始,其实中国精神里头都倡导行动,倡导这样一种行动,到了史记作者司马迁,前后还有《山海经》、《水经注》,这都是靠行走走出来的,它不是说凭空想那个地理位置什么的,这些文化的遗产都是靠行走。到了这个唐代盛世,它同样还不是关起门来,还是要开放的,比如说唐高僧玄奘,他的《大唐西域记》,也是靠行走,就是说取经的这样一个行走道路,他最后产生了这样一部巨著。到了明末,顾炎武。一直到清代,近代,都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行走是古代的行走的一种延续。包括余秋雨,他对中国文化的脉络,就是通过行走来把握,《文明的碎片》里的他已经把行走文学从身体的意义上提炼到一种精神的意义上。我还是打算这样走下去的,因为我受益于它,对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开拓作用。原来念书的时候,作为一名学者来说,好静不好动,思维会容易陷进去,而且容易成为一种管状思维,狭窄的一种,往深里头的,就象打井一样,这个当然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揭示生活物质世界提供给你的,去感悟它,然后把它抓过来,然后写入文字,再给别人看。我觉得这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上是一种拓展,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吧,一个,读万卷书,一个,行万里路。后者,可能也更帮助我更深地读。
20、你更喜欢哪一类绘画作品?是抽象还是具象,是西洋画还是国画?
何:还是更喜欢具象的一些东西,油画接触的比较多一点,咱们省里的王宏剑,二段,曹新林这样一些画家,他们其实都是具象的一种东西,抽象的东西比较少,可能跟我欣赏习惯有关。具象里头也有创造,比如说段正渠的东西,他画那个《东方红》,画陕北汉子在唱,那样一个人的脸,瘦瘦的,戴着羊白的毛巾,在那儿唱,他那个已经不是单纯的那种照相,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一种摄影的绘画,而是把人夸张了。他那个具象里头也有表现主义的东西,写实和表现结合得非常好。
21、你肯定有许多藏书,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收藏爱好吗?
集邮。但是好多邮票都丢了,历史也比较短。
22、你有着极具亲和力的外表和给人以安静的语言,除旅行外,曾想过有冒险和刺激经历的冲动吗?
何:漂流我还是很喜欢的。八十年代,第一次黄漂,洛阳的雷建生他们,那时候我就想跟他们一块儿去。正读大学,87年,当时捐款,捐物给他们,每天从电视里关注他们的行程。内心里头还是有这样一种冲动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比如说余纯顺,我写过一篇文章,《远方谁在赶路》,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上海男人,在文化上来说,北方男人不太看得上,但他就是走出了一个汉子。那种沿着中国大地一直在行走,一个人徒步,也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火车啊,汽车啊,自行车都不要,我觉得他那个里头有一种很动人的少年精神。我当时在文章里写到了这种少年精神。他在倡扬一种自然,回到一种本真。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贵。
23、面对鲜花、掌声,你感到过压力吗?
何:也有压力。觉得真实的状态是有压力的。鲜花,掌声,它是一个句号,等于把你以前的东西给你隔开了,那么在这个句号往前再走。 如果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你可能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变成一个公众人物以后,可能别人会对你提出要求,起码对你有一种期望值。压力也是动力,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24、你祖籍是安徽,生长在河南,你更喜欢黄梅戏或者是豫剧?
何:我听的黄梅戏和豫剧都不多,京剧可能还多一点。但两个剧种都不是太一样,豫剧比较高亢,黄梅戏比较委婉。黄梅戏歌颂爱情比较多,豫剧呢,关注女性当中的豪杰人物。我可能更喜欢宛梆和绍剧,它那种高亢,那种在那种历史上女性受压抑的叛逆,非常高亢的一种亢奋,调子非常,顶的非常高,有很强的冲击力。宛梆呢,很偶然,我在南阳邓县下乡,听一个流动戏班子,在搭的棚子里唱,夜里传得很远。那种沉郁我一生都忘不了,那种好象高亢沉郁结合起来那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有一种洗心的作用。
25、你获得了“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和“鲁迅文学奖”,在这个领域,你取得了国内的最高奖项,你会寻求向别的领域发展吗?
何: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其他领域,机会可能没有吧,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曾经想过一定要拍一部电影,当一次导演,觉得不当一次导演有点可惜,想拍一部关于孔子的传记,看《甘地传》,它把它那个民族的,印度这样一个大地,这样一个民族的一个精神领袖,给它写出来了。所以也想把孔子这样一个人物,或者象鲁讯这样一个人物,通过电影,当然这个影视的表现很多了,象鲁讯,很多电视剧,表现很多了,但是想用一种传记与史诗的方式提炼出来,把巨人的思想民族的精神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来, 只是想法,尚待机会。
26、你喜欢哪一类体育运动?
何:现在体育活动比较少,现在主要是散步。原来喜欢打羽毛球,网球。
27、是机遇>勤奋,还是勤奋>机遇?
何:勤奋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对个人来说,不可能去要求机遇,只能是要求勤奋,只能是勤奋累加到一定程度,机遇才会来敲门。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机遇勤奋都存在,但是对于我们这代来说,遇到了最好的机遇,和平年代,稳定,民族整个在向上走这样一种时候,我觉得确实对每个人提供了最大的一种成功机遇,只要你能够勤奋,只要能够把握,都会获得理想,成功,证明自己的价值。随着入世之后,我觉得可能机遇提供的空间更大,感觉自由度可能更高,选择机会更多,但这个时候,一定得勤奋,不能抱有投机取巧,机会主义的心理。这样也才不会错过机遇。
28、关心网络生活吗?
何:上网是每天都上,看新闻。健康,时尚,旅游,还有一个地理栏目,有时候也去浏览一下。聊天很少。网络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发信,也是通过网络,快。
29、谢谢你能光临河南省社科院网站,你能对关心你的网民说上几句话吗?
何: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希望大家都能关心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把握机遇,心想事成。
30、最后我代表网站全体同仁祝你今后事业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何:谢谢!








